时间: 2024-10-20 17:26:42 | 作者: 合金铸钢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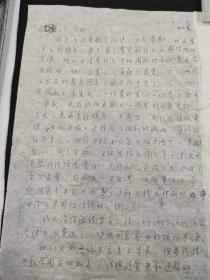
2011年初夏,当刘武、同号文两位中国学者,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物馆打开近一个世纪前封存的周口店化石的时候,往事像一张老照片,逼真地展示在眼前。
1918年是周口店挖掘的起点,此阶段瑞典人开创并主持着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这期间,先后有400多箱采自中国北方的动物化石及文物标本,从港口出海运往瑞典,后来成为两个瑞典博物馆展品的主体,其中先后清理出三枚古人类牙齿,特别是最早清理出的两枚牙齿,曾引发了世界级的轰动
在发掘周口店之前,欧洲学者在亚洲寻觅古人类的历程,是从一场科学悲剧开始的。悲剧的主角是一位名叫杜布瓦的年轻荷兰医生。
与达尔文几乎同时代,一位名叫海克尔的德国学者,在赞同进化论的同时,不赞同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提出从猿到人中间有一个缺环。“海克尔认为,这个缺环是一种没有语言的早期猿人。”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说。
作为进化论的拥护者与海克尔的信徒,杜布瓦将寻找“缺环”的目的地锁定在东方。1887年,他以荷兰军医的身份,在印度尼西亚登陆,一边行医,一边进行挖掘。
1890年~1891年,杜布瓦的发掘工作终于产生了“惊人”发现,他在爪哇特里尼尔先后找到了一颗臼齿、一件头盖骨、一根大腿骨。他认定,这就是进化的缺环。
“从大腿骨上能够准确的看出,这是一种直立行走的猿人,因此杜布瓦将其命名为直立人。”吴新智说,“后来,有一些学者习惯性地称之为爪哇人”。
然而,不幸的是,当杜布瓦在欧洲宣布他的科学发现时,他受到了科学界,乃至社会舆论的种种非议与围攻,有人甚至嘲笑说,杜布瓦从特里尼尔带回欧洲的,不过是“白痴”、“畸形人”的头骨。
处在论战中心的杜布瓦渐渐吃不消了,他先是三缄其口、步步为营,后来索性把化石带回家乡,埋在地下。
到了20世纪20年代,杜布瓦终于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声称自己在特里尼尔找到的,不过是一种大个头的长臂猿,与人类的谱系无关。此后,他一直维持着这一观点,直到1940年去世。
一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在评价杜布瓦的悲剧时说,“他出生得太早”,“地点也不幸地选在了印度尼西亚”。
到了20世纪初,西方学者中又出现了一种假说,认为中亚很可能是孕育人类的“伊甸园”。一时间,西方学者纷纷涌入亚洲。其中,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收获。
1914年,时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安特生,受到北洋政府的聘请到北京出任农商部矿政顾问。在华10年间,他除了矿政专业外,在考古发掘上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1918年,一条线索将安特生带到了周口店。对鸡骨山进行了三天考察后,他开始组织在周口店进行小规模挖掘。然而3年间他并未找到人类化石。
1921年,安特生的“后援”来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古生物学者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协助安特生的挖掘工作。
同年,在一位当地老乡的指引下,“北京人”的“洞府之门”,向他们打开了。此后,师丹斯基在这个地点,挖到了周口店出土的第一件人类化石 一枚臼齿。
1918年开始,从周口店以及中国北方别的地方出土的发掘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往瑞典,先后共400余箱。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博物馆及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两家瑞典博物馆,就是靠着周口店出土的化石,而名气大增。
1926年,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清理从周口店运来的发掘材料时,又发现了一枚前臼齿,这是最早的两枚牙齿。
瑞典人早期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是在瑞典皇家的支持下进行的。安特生在华的考古经费大多数来源于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当时的瑞典皇太子,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
1926年,瑞典皇太子访华之际,安特生正式公开宣布两枚牙齿的消息,从此周口店引起世界关注,“北京人”作为早期人类的代表,也为世人所知。
1974年到1979年间,黄慰文曾“坐镇”周口店主持日常工作。他自己戏称“当了5年寨主”。
这5年间,他接待了到周口店参观的各色人等,其中颇有国际上叱咤风云的政坛要人。1977年,他从一位瑞典客人那里得知,上世纪50年代,师丹斯基在清理周口店材料时,又发现了一枚人类牙齿 一枚前臼齿。
5年寨主生涯孤独、寂寞,黄慰文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其实是当了5年和尚。”在这5年间,他一边主持工作、接待要人,一边整理周口店的历史文件,并协助贾兰坡撰写《周口店发掘记》。
由于与周口店的“亲密”关系,多年来,他常常被媒体“骚扰”,要他解答“北京人的头盖骨到底在哪里?还能找回来吗?”这类的疑问。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7年是一个分水岭。这期间在加拿大人步达生的主持下,大规模发掘真正开始,中国学者也参与到发掘工作中。
1927年到1937年是周口店发掘的黄金时代,共采集1221箱发掘材料,其中人类化石近200件,包括5个较完整的头盖骨和多件头骨破片。
这一阶段的发掘经费主要由美国支持,瑞典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参与此阶段的发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到周口店的交通中断,周口店十年的黄金期就此结束。
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日军便占领了北平城内的美国机构,这中间还包括曾经存放“北京人”化石的协和医学院。
多年来,老一代学者曾从战乱后残缺不全的文献,以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寻找线索,寻访失踪化石的下落,均未能如愿。
时至今日,寻找“北京人”,依然是一个国际热点话题,而黄慰文对《科学时报》记者说,那是个战乱年代,时间也过去那么久了,种种“北京人”重现的惊人消息,有些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有些不过是媒体戏剧化的炒作。
在黄慰文看来,在一个战争年代,一个特殊时期,“丢失了恐怕就丢失了,再也难以找回”。
因此,2011年初夏,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在清理1920年前后的周口店发掘材料时,意外地鉴定出了保存于瑞典的第四颗牙齿时,新的希望又出现在人们面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对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得以重新开始,而1937年前的黄金盛世却再没有出现。
“从1949年到1966年十几年间,发掘出的人类化石只有6枚单独的牙齿,一件带有一枚牙齿的下颌骨前部和一个头盖骨的前部和后部。”吴新智说,“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北京人”化石材料。”
周口店运去的发掘材料,曾让瑞典的古生物学家们一度忙碌起来。然而,清理工作在师丹斯基发现了第三枚牙齿后不久,就日渐荒疏了起来。
近两年,瑞典人再次“想起”了尚未清理的几十箱材料。几个月前,清理工作忽然出现“惊人”发现,一个未成年人的头盖骨惊现于人们面前。
荒疏多年,面对如此“重大”的发现,瑞典人决定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协助鉴定。
这是自1918年以来,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受邀参与运往瑞典的周口店材料的清理、鉴定工作。接到邀请,古人类学家刘武、古哺乳动物学家同号文,一起前往瑞典。
两位经验比较丰富的学者到场后,通过对头骨形态、出土层位,通过对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做多元化的分析后,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个幼年头骨,应该是考古中常见的晚期“混入品”。
既来之则安之,在瑞典期间,刘武、同号文与瑞典学者一起,对周口店的材料来清理。
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短短几天的工作,两位学者居然不虚此行,有了意外的收获:第四枚牙齿 一枚人类犬齿,出现在眼前。
“这是目前存世的11枚北京人牙齿中,唯一一枚犬齿。”刘武对《科学时报》记者说,目前这颗牙齿在科学上的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从学术上说,每一件新材料问世,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潜在价值。
早年的研究,由于研究水平、方法、思想有着时代的局限,“如果那些化石不丢失的话,以现代手段重新进行研究,应该会有新的收获”。
因此,这枚牙齿的出现使人们对瑞典未开封的40箱物品燃起了新的希望:从这40箱中,我们还能找到些什么?
上世纪20年代的香烟盒、洋铁罐包裹、存放着化石;繁体中文、老式拼音与英文对照标签,书写工整“一段尘封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